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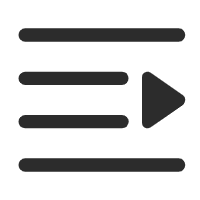 散文
散文  首页 > 新闻中心 > 特辑 > 散文
首页 > 新闻中心 > 特辑 > 散文
故乡蝉鸣
盛夏,蝉鸣四起,叫得起劲儿。蝉在白天叫,在温度高的时候叫,从清晨到傍晚不停地叫,我嫌它聒噪,却剔除不掉。整个村庄被蝉鸣声充斥着、包裹着。
就像古人诗中对蝉描写的那样:“垂緌饮清露”“居高声自远”,蝉在高枝之上傲视群虫,叫声响亮,回荡在树木间。蝉的鸣叫声充斥着整个夏天,怎奈它们只有一个音符,唱得太单调,没有间歇、没有停顿、拉着长音,我总是替它上不来气儿。入伏后,杜梨树上的伏里鸟也在 “伏里儿、伏里儿”地叫着。尽管伏里鸟的嗓门也很大,怎奈寡不敌众,大片的蝉鸣声压倒了伏里鸟的叫声。它们的叫声就像三伏天里的合唱,蝉唱的是高声部,伏里鸟唱的是低声部,伏里鸟的叫声,成了蝉换气时人们才能听到的点缀的音符。至于平时的那些鸟鸣声,直接被我们的耳朵忽略掉了。
其实,一场大雨便可以让它们噤声,在难得的安静的间隙,清理一下杂乱的闹哄哄的思绪,拔锄内心随盛夏疯长的杂草。
说到蝉鸣,我就会想到那个小的不能再小的小学。学校在村东的一个胡同里,教室是几间土坯房,房前是一片干净的连一棵像样的树都没有的空地,只有角落里随一场场雨钻出并渐渐长起来的小榆树和小枣树,叶子嫩绿,在阳光下透着亮。
李方石老师是一个斯文的老师,说话慢条斯理、温文尔雅,喜欢穿浅灰色或灰白色的上衣、深色裤子,而且一尘不染,像是从古代私塾里走出来的先生,如果穿上长袍大褂就更像了。我们几乎未见他发过火,未见他训斥过谁。在查阅资料之后,他半白话半文言地对我们说:蝉是“善鸣之虫”,幼虫生活在土壤里,吸食植物的根,成虫吃植物的汁。蝉之所以能鸣叫,是因它腹部有一对鸣器,鸣器只雄蝉才有,雌蝉是“哑巴”。至今,我仍记得他关于蝉的解释。
小时候,我们只放麦假和秋假,不放暑假。于是,夏日,伏天,我们便有了悠长的午后时光。
李方石老师在上午放学前总是叮嘱学生们:中午在家好好午睡,男孩子不能去下湾,否则要挨戒尺的惩罚。父母也再三嘱咐,可那时哪有一个孩子肯听话呢。
下地干活的大人们是必睡午觉的,小孩子们假惺惺地躺下,待父母的鼾声一起,便蹑手蹑脚地背起书包,灌上一瓶水准备往外溜。那时候没有现在这样的保温杯,我们把用过的输液瓶子洗净,或者把盛过醋、啤酒的瓶子刷洗干净,灌上凉白开水,然后在瓶口塞上橡皮塞,便偷偷地溜出去。
仿佛是不约而同的,男孩子晌午大都去村西的大湾里游泳。一个个光腚猴跳进大湾,水面上露着一顶顶黑色的小脑瓜,他们在水里追逐嬉闹,不亦乐乎。我们三五个女孩子到树荫下玩耍,在树干上捉知了壳,能卖钱,有串乡的人来收,听说那是药材,叫蝉蜕。伴着聒噪的蝉鸣声,我们一中午能捉好多知了壳呢。
快到上学的时间了,男孩子们急匆匆地从湾水里钻出来,用背心或褂衩胡乱地擦干头发,再去学校。背心在燥热的夏风中,一会儿就干了,似乎没有了下湾的证据。
尽管他们装作没事人的样子,可当天谁有没有下湾,老师自有辨别的办法,用手指盖儿在胳膊上一划,有道白印儿,那必是又偷跑去下湾了。因为不会水的孩子常常出事儿,老师担心不安全,所以上课前会让他们罚站、用戒尺打手心,被打手心的男生,低头咬着嘴唇,抠着手指甲,不敢抬头看老师的眼睛,也不敢说疼。也许是惩戒的作用,男孩子们心里有了敬畏,就算是偷着去游泳,也很注意安全,都平安无事。
下午放学后,天气渐渐凉爽一些的时候,我们便伴着蝉鸣声去地里拔草了,大家都很卖力,拔的草背回来,一半喂羊、喂牛,一半交到学校里。我们喜欢交青草时被李老师微笑着、抚摸头发表扬的感觉。卖了这些草,李老师买粉笔、黑板擦,给我们买演草本、作业本和铅笔。
我们拔的草摊晒在教室前的空地上,清徐徐、甜丝丝的青草味儿钻入鼻翼、沁人心脾,蜻蜓、蝴蝶围着半干不干的小山般的草堆上下翻飞,而蝉鸣声是始终环绕着我们的立体背景音。
说句实话,我不太喜欢蝉鸣声,有些聒噪,但我却喜欢它们变成蝉之前蝉蛹的样子。在变成蝉之前,我们叫它“戒留爬儿”,逮“爬爬”是伏天最大的乐趣,晚上打着手电,顺着村前的柳树、杨树、榆树找去,一般柳树下最多。那时我可是逮“爬爬”的高手。雨后、傍晚或者夜里最多,用手电筒照亮,有的伸手就能捉到,有的已爬到高处,我便“蹭蹭蹭”地爬上树,就算正在蜕变的幼蝉,也统统被我拿下。
雨后,是逮“爬爬”的最好时机,地皮上有个小洞,一抠就大,扒开泥土就是惊喜了!当你伸进手指,一枚肉嘟嘟的“爬爬”被你扥出来,小爪爪不停地挠你,挠的手指肚和手心儿痒痒的,而且手上常常被“爬爬”的尿液染成灰黑色。一晚上能逮满满的一罐头瓶,拿回家,洗净,用盐水浸泡,第二天中午,经过油炸,成为我们香喷喷的盘中餐,咸香酥脆,是令人垂涎的美味!童年,没有多少肉食,油炸“爬爬”调剂着我们的三餐。
与蝉鸣同在的,有黑色夹手的“老牛”、五星瓢虫、看家护院的大白狗、院子里的老黄牛、地上到处觅食的鸡鸭和袅袅的炊烟。
儿时的乡村,在我记忆的底部鲜活起来。
院子里,青草的香气混杂着牛粪的气味,裹挟着炊烟的气味。下地回来的大人们掰回几只玉米棒子,灶膛的火苗儿舔着锅底,干燥的棉柴在灶火中啪啪作响。大锅里煮着青绿色的毛豆、饱满的花生、锅底下烤着金黄的玉米。喜滋滋地啃着烤熟的玉米棒子,嘴巴周围黑黑的,像一圈黑胡子,显得满嘴的牙雪白。
晚饭后,家家户户都在院子里铺上凉席乘凉。一茶盘切好的黄瓤起沙的西瓜、一壶粗茶水,一把芭蕉叶做的大蒲扇扇来阵阵凉风,听着收音机里咿咿呀呀地唱着“花木兰羞答答,施礼拜上……”,白天劳作的疲劳一点点褪去。蝉鸣渐弱,丝瓜架上挂着的蝈蝈,叫声愈加响亮,丝瓜和扁豆的气味飘过来,那是人们最惬意的时光。
那时,没有电视、电脑、手机、微信,是我们与天上的星星最亲近、交流最多的时候,我们都是数星星的孩子:“牵牛星”“织女星”和像勺子一样的“北斗七星”……我们清澈的眸子总能看到星星一闪一闪地冲我们微笑着眨眼睛。
……
在蝉的叫声中,指甲桃红了,丝瓜花黄了,扁豆花紫了,芝麻花白了,玉米棒子熟了,夏日的意蕴浓了。
枕着蝉鸣声入睡,我们可以尽情地做一个热乎慵懒、踏实温馨、没边儿没沿儿的悠长的梦……